虚实合一的元宇宙:数字现实可以直接植入肉身大脑吗?
把合成的体验上传到大脑一度是科幻的幻想,但新的脑机接口正在让它变成非虚构——当然,这个进程会非常缓慢。
神译局是36氪旗下编译团队,关注科技、商业、职场、生活等领域,重点介绍国外的新技术、新观点、新风向。
编者按:现在人类对大脑信号做出解析已经取得了不小进展。而反过来,给大脑写入信号,让人产生感知也有一些突破了。比方说,通过给特定神经元植入电极发送电脉冲,可以让人产生看到光点的感觉,尽管其实并没有光点的存在。那我们能不能像《黑客帝国》一样,在人的大脑里制造出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呢?也许可以,但就算我们最终生活会在同一个《黑客帝国》里面,却仍然仍然处在不同的世界里面。何谓孤独?孤独的意思,就是就像我没法理解拥有翅膀和用回声定位是什么感觉一样,我永远也没法完全理解你所经历的事情。文章来自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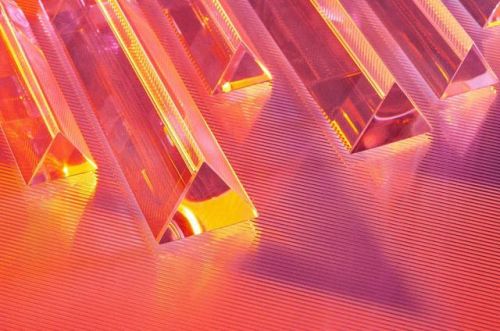
划重点:
把信号写入大脑可以制造感知
你感知到的的东西未必总是“真实存在”——它只存在于你的头脑
信号跟想法是两码事,读取和写入大脑完全不对称
我们可能最终生活会在同一个《黑客帝国》里面,但我们仍然处在不同的世界
一、把合成体验上传大脑
一个年轻人,身穿着灰色法兰绒长袍,正在平静地坐在一张桌子旁,面前是一个毫无特色的黑盒子。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帽子,看起来像是用纱布绷带做的。有一束电线从里面盘出来,最后出现在他的后脑勺那里。他正在等着什么。
一名穿着白色实验服的研究人员走到桌子旁,默不作声地站了一会儿。那男人盯着这个盒子。等了一会儿,但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那个男人眨了眨眼,显得有点不安。研究人员便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就在第一秒钟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只眼睛——一只眼睛,还有一张嘴。”
研究人员把盒子换成了不同的物体。这次是个橙色的足球。他们敲了一下,很明显,这个男人的脑子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我该怎么解释呢?就像上一次一样,我看到了一只眼睛——一只眼睛和一张嘴,侧面的。”
从严格的意义来说,这个人是一个赛博格(电子人)。他那梭状的脑回,沿着大脑底部两侧分布的隆起的皱褶上布满了电极。这些电极是他的医生植入进去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有助于追踪这名男子癫痫发作的原因。但电极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不仅可以让研究人员读取来自大脑的信号,还可以将信号写入大脑。麻省理工学院的Nancy Kanwisher正在领导一群神经科学家,她们在研究所谓的梭状回面孔区(这个区域因人看到脸部时会变得活跃而得名)。她们的问题是,如果她们把水泵反转会怎么样?也就是故意去激活那个区域的话——那名男子会看到什么?
你不需要变成赛博格才能知道你永远不应该相信自己那会说谎的头脑。比方说,它就对你隐瞒了一个事实,其实你的所有感知都是有延迟的。将光子转化为视觉,气压波动转化为声音,雾化分子转化为气味——然后,你那不完美的感觉器官需要时间来接收信号,将它们转换成大脑的语言,然后再把它们传递给灌木状的神经细胞网络,由后者计算传入的数据。这个过程不是瞬间完成的,但你永远不会意识到无数的突触正在传递,这些嘶嘶作响的电化学构成了你的想法。事实上,这是一种舞台艺术——而你既是导演,又是观众。
你感知到的,或者你以为自己感知到的东西未必总是“真实存在”——它只存在于你的头脑,而不在任何其他地方。梦就是这样。迷幻药就干这事儿。当你想象自己姑妈的脸,自己的第一辆车的气味,或者草莓的味道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从这个角度来看,把感官体验——认知的一种——摄入某人大脑其实并不难。在本文的前面这几段里其实我已经对你做了这件事了。我描述了赛博格的穿着,暗示了你房间是什么样的,告诉你足球是橙色的。你在自己的脑里已经中看见了,或者至少看见了它的某个版本了。你也听到了(用你大脑的耳朵)研究对象在跟科学家交谈(尽管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说的是日语)。这种植入法不错,很文学。但是如果有更直接的航线会更好了。大脑就是一种有点咸的,将感官信息转化为思想的黏性糊状物;你应该能够利用这种能力,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跟现实无法区分的模拟世界。
Kanwisher 的实验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还差得远。但它确实让人看到了直接将信息植入大脑的可能性与威力。如果你看过那个测试的视频,最值得注意的是那名男子的温和反应。科学家在操作的时候,他似乎没有任何感觉。长眼睛的盒子似乎没有吓到他;事实上,当它消失时,他似乎更惊讶。确切地说,这种体验可能不是真实的。(有一次,Kanwisher曾告诉我,志那位愿者问,“我是不是只是在想象?”)但这件事里面还有有些真实的东西的。进入到他的梭状脑回的电脉冲循环不仅让他看到了一张脸,还注入了难以形容的面孔的感受。
把合成体验上传到大脑,这个想法一直是科幻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有75年的历史了——例子当然包括《黑客帝国》,还有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 的大部分作品,网络空间,元宇宙,1983 年的电影《尖端大风暴》(Brainstorm)里面的磁带录音机,(被低估的)1995 年上映的电影《末世纪暴潮》(Strange Days)里面的超导量子干涉装置等。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距离在每个人的脖子背后都有一个数据端口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神经科学家已经可以很好地对从大脑发出的信号进行解码,也可以移动光标或机械臂了(尽管还没法做到像生物连接那么流畅优雅)。但植入信号进去要比这棘手多了。
二、电极植入法
神经外科医生倒是非常擅长植入电极。问题是要知道植入到什么地方,因为你要面对的是还非常神秘的神经灌木丛。虽说一小部分的细胞也许只处理特定任务的特定部分,但细胞群之间还会相互交谈,而正是这些网络的形成和重组帮助我们有了认知能力。如果你打算欺骗大脑,让后者把人为构造的输入感知成现实,就必须了解单个神经元做了什么,一大群的神经元又做了什么,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这牵涉到的东西就太具体了,也许具体到令人沮丧。16 年前,艾伦脑科学研究所(Allen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的首席科学家Christof Koch曾帮助做过一项现在已经很出名的研究。这项研究表明,大脑里面有一种叫做内侧颞叶的神经元,这种神经元会对文字工作者所谓的名词(人物、地点、事物等)做出反应。比方说,当一个人看到女演员哈莉·贝瑞的照片时,这个区域就会被激活起来。换成女演员詹妮弗·安妮斯顿的不同照片(但不是她跟布拉德·皮特在一起的照片)时,该区域也被强烈激活了。Koch说:“神经元是感受的原子。对于类似《黑客帝国》里面的技术来说,你必须了解每一个神经元的触发特征,而大脑里面一颗米粒大小的区域就有 50000 到 100000 个神经元。” 他说,如果没有这本(神经元会促发特征的对照)目录,你也许能让某人“看见闪光或动作”,但他们“永远也看不到圣诞老人。”
好吧,看见闪光也是个开始。闪光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在荷兰神经科学研究所(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Neuroscience)的实验室里,Pieter Roelfsema 和他的团队一直在用闪光来教猴子阅读。哲学书猴子还看不了,但已经足以能够区分字母表里面的字母。研究人员是通过刺激所谓 V1 区域来做到这一点的。这块区域属于视觉皮层的一部分,是长在每个灵长类动物头部后方的一块神经元。一旦通过 V1 电极发送电流,哺乳动物就会看到一个漂浮在空中中的光点。切换到隔壁的电极,第一个点旁边就会出现第二个点。这些是光幻视,就是你撞头之后看到的那种火冒金星,或者大笨狼(Wile E. Coyote)被痛殴后在他周围飞来飞去的小鸟。(那位日本患者产生的感受被正式叫做“脸幻视(facephenes)”。)
Roelfsema 说,将一组电极植入到 V1之后,“就可以像矩阵板一样使用了。如果有 1000 个电极,基本上就相当于有 1000 个灯泡,而你可以在数字空间里面点亮这些灯泡。” 这支团队可以刺激电极,模拟出字母 A 或 B 的形状,而猴子能够表明自己看到了不同。
当大脑在做大脑的事情时,你看到的信号其实并不是想法;那是大脑在思考时排出的废气。
但这项技术也让你有了想象的空间,比方说视障人士最终如何可以通过这项技术看到一些东西:把 V1 的电极矩阵连接到外部世界的相机,然后把镜头处理成现实的点画图。这幅画看起来也许有点像位图版的 Minecraft,但大脑是非常擅长适应新的感官数据的。
尽管如此,为了有足够多的点来做成线与形状,以及其他的有用刺激,得提供大量的电极,而且每一个电极都需要非常精确地定位。任何电极型的方案,只要目标是把可理解的信号(而不仅仅是闪光的幻视形状)传送给大脑,就都得这样。不管想法是什么,都跟神经相关。Kosh说,稍微多刺激了一点组织,“你会陷入混乱。” 更重要的是,你还得把握好时机。感受与认知就像钢琴奏鸣曲;每一个音符都必须按特定的顺序发声,这样音乐才会和谐。要是搞错了时机,相邻的电脉冲看起来就会不成形状——而是像一大块污迹,或者就像什么都没有一样。
刺激大脑的位置与时机为什么如此难以解析?部分是因为如果你试图诱导神经活动的话,记录神经活动产生的数据并不能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科学家 Jack Gallant 说:“大脑的读与写完全是不对称的。”当大脑在做大脑的事情时,你看到的信号其实并不是想法;那是大脑在思考时排出的废气。当感受越过终点线时(编者注:将感受的形成比喻为赛跑),研究人员能获得关于大脑整体状态的一小部分数据,但把这些数据回送并不能重建整场比赛——从感觉、感受、识别到认知要连跑数圈。是,Kanwisher 的团队确实激活了大脑的一大块面部识别区域,让某人看到了一张脸,算是吧。但那是感性(sensibility),不是感觉(sense),不是对特定面孔的感知。看到詹妮弗·安妮斯顿会刺激詹妮弗·安妮斯顿神经元;但没人知道刺激詹妮弗·安妮斯顿神经元能不能让人看见詹妮弗·安妮斯顿。
目前获批用于人身上的电极阵列均无法弥合这一差距。这些阵列体积庞大,但最多也就只有大约 1000 个电极,按照大脑的定义,这种充其量只能是低保真版。目前,研究人员距离演奏出令人信服的奏鸣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神经外科医生 Daniel Yoshor 说:“现在我们的水平相当于会敲键盘。”但技术当然还会改进。Yoshor跟同事已经获得了五角大楼的那个疯狂科学机构 DARPA的资助,他们打算先开发了一个有 64000 个电极的阵列,而下一个目标是有 100 万个电极的阵列。埃隆·马斯克的Neuralink 正在研究更轻薄、更灵活的植入物,以及可以将这些植入物植入到大脑里面的机器人外科医生。到了遥远的未来,也许会实现只有一粒沙子大小的无线联网微芯片,或能嵌入 1 亿个电极的薄片,而且每个电极都能连接到自己的处理器,就像电视机里面的像素一样。也许还植入不了勃拉姆斯的音乐,但是做出你听了想跳舞的东西还是有可能的。
三、“全息光遗传学”
就算能够把十亿个电极塞进去,仍然会遇到问题。也许你可以把材料做得足够柔软,就算有人摇头太过用力,也不会造成组织损伤。也许你可以找到从大脑那粘稠的保护细胞(叫做神经胶质)那里脱落的表面涂层。但还记得大脑其实就是悬浮在咸水之中的一团凝胶状的思想肉块吗?嗯,咸水是具有很高的导电性。西北大学材料科学家John Rogers说,通过电极发送电荷,希望能刺激一个神经元,但这个神经元还会“延伸到电极所刺激的神经元以外的区域,而这个空间区域的维度我们仍然弄不清楚。也就是说,你点亮的也许不止一个神经元。” 每一个电极就像大雾弥漫的黑夜里的灯塔:它确实照亮了岩石与浅滩,但光线也会在大雾中衰减和衍射。这种信息传递确实是没法控制的。
不过,另一种技术也在开发当中。它的基础是一种变形色素蛋白,叫做视蛋白。脊椎动物的视网膜细胞里面就有这些分子;一旦被光线照射到时,视蛋白就会忙作一团,变成一个新的形状,这会在细胞内引发一连串的鲁布·戈德堡反应,最终形成一股电脉冲,并被发送给大脑。你懂的,这就是视觉。但是你不需要眼睛才能使用视蛋白。对于部分藻类和微生物来说,视蛋白就嵌入在细胞的外表面,充当对光敏感的通道,将离子移进移出。(没有大脑的单细胞生物就是靠这种方式朝着太阳游动的。)
这一点非常有用,因为神经元也是这么工作的——传导离子及其携带的电荷。 2000 年代中期,研究人员想出了怎么将这些外表面的视蛋白基因移植到脑细胞里面的办法。就是这方面的工作,使得神经科学家可以用不同颜色的激光去控制特定种类的神经元——也就是可以小心翼翼地打开和关闭特定的神经元!如果你想给一种很酷的大脑控制技术起名字的话,再也找不到比“全息光遗传学”更好的了,真的。
这项技术非常适合研究不同的神经元都是干什么的。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基因工程的方式将离子门植入到整个神经元网络,包括大脑里面的各种细胞里面,这种方式无论是破坏性还是物理的侵入性都要比塞个插头进去要小一些。(反过来,除非你把光纤直接塞进去,否则很难让光线深入穿透进去。)在某些情况下,通过采用不同的技术,细胞也可以在光源下发出荧光,从而让研究人员能够在显微镜底下观察工作中的大脑情况。
但光遗传学也适用于输入。可以用光猝发(来自激光、数字投影仪的光、通过光纤植入大脑)来触发所设计的离子门。来自纽约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已经培育出一种小鼠,这种小鼠的嗅球(脊椎动物前脑结构中参与嗅觉的部分,位于老鼠敏锐的鼻子与皮质之间,用于感知气味)是做过了光遗传学上面的优化的。当科学家在合适的时机把适当种类的光照射到嗅球上面时,老鼠就会闻到(或表现出像是闻到了)他们所谓的“合成气味”。
你可以做出一个功能齐全的模拟世界,可以涵盖所有的感觉,但它最终的样子怎样,感受如何,这些始终都要取决于你的想法。
那种气味是什么味道?纽约大学神经生物学家Dmitry Rinberg回答道:“我们不知道。也许很臭。也许很宜人。也许是它在这个宇宙里面都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气味。” 他说,你没办法知道。你又不能问那只老鼠。
不幸的是,这是确保任何一种感知输入系统是否有效的唯一方法。你得问佩戴者(所有者?接收者?如果植入物是遗传性的,但还加上一条激光的话,你还是赛博格吗?)的感受。此外,就算植入的是光纤而不是电线,但他们头上还是要插入线缆。而且他们还必须自愿对自己的大脑进行基因工程。
就这方面而言,对人类的外围所做的工作比对大脑所做的要先进得多。人工耳蜗植入进去的是听觉神经而不是大脑,但却能给听力受损的人提供了非常好的体验,虽然在保真度方面还比不上健康的耳朵。一些科学家正在研究效果等同于视网膜的东西。有的假肢连接上神经之后就可以传递触觉。给假肢增加一点振动甚至可以制造出运动感觉的错觉,一种手臂在空间里面移动的感觉,这样用户不用看假肢也知道它在哪里了。
但这些都不是完整的感觉器官。这不是一个世界。跳舞的幻视,人工耳蜗输入,神经光子激活嗅觉皮层——哪怕你能够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装进头骨——那也没法让你以为自己是在别的地方。这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会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构建现实。你可以做出一个功能齐全的模拟世界,可以涵盖所有的感觉,甚至是非常难以捉摸的感觉,但它最终的样子怎样,感受如何,这些始终都要取决于你的想法。
1974年,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发表了一篇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论文,题目叫做《变成蝙蝠会怎样?》。论文指出,每一个有意识的生物的体验都是个体化的,对于动物及其大脑来说,这种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何谓孤独?孤独的意思,就是就像我没法理解拥有翅膀和用回声定位是什么感觉一样,我永远也没法完全理解你所经历的事情。即便我们是真正的赛博格,我们的后脑勺装上了插头,我们的皮层植入了电极和光纤,准备好接收装满了发绿光的汉字的数字红色药丸,我的大脑对所有的输入的解释也会跟你的大脑不同。当然,我们会告诉我们的机器霸主,我们正在体验着同样的东西,因为这就是感受。但是,我在挠你的梭状回时,你看到的那张脸,永远不会跟你在挠我的梭状回时看到的那张脸一样。我们可能最终生活会在同一个《黑客帝国》里面,但我们仍然处在不同的世界。
译者:boxi。